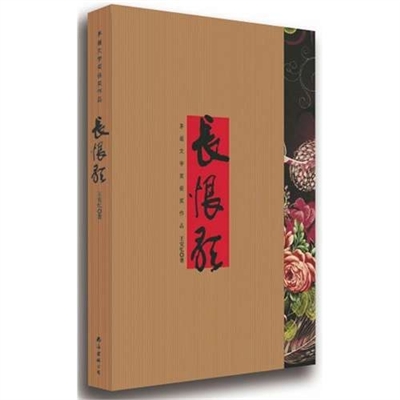“有时候,拥有梦想也要付出代价——一生坚守美丽、坚守青春的王琦瑶,却死得那么不堪……”几年前,读王安忆的《长恨歌》,我写下这样的感受。时至今日,再读《长恨歌》,感觉其中的“恨”字,也许只是深深的遗憾:
生活在弄堂里的一个典型的上海女人,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,四十年,历经沧海桑田的变迁,沉垒了无数理想、幻灭、躁动和怨望,从未放弃过对美丽与爱情的追求,最终没有得到心爱男人的相守相伴,却因钱财的缘故,被女儿同学的男朋友杀死。由此看来,王琦瑶的“恨”,当真是绵绵无尽期吧。
在《长恨歌》中,女作家王安忆以细腻而绚烂的笔触,构建出一个庞大的空间与时间流程,叙述了上海的历史,刻画了上海的女性,审视了上海的文化。可敬的是,无论多么庞杂的叙事,她都是笔墨从容、娓娓道来——
“上海的弄堂是很藏得住隐私的,于是流言便漫生漫长。夜里边,万家万户灭了灯,有一扇门缝里露出的一线光,那就是流言;床前月亮地里的一双绣花拖鞋,也是流言;老妈子托着梳头匣子,说是梳头去,其实是传播流言去;少奶奶们洗牌的哗哗声,是流言在作响;连冬天没有人的午后,天井里一跳一跳的麻雀,都在说着鸟语的流言。”
整本书都很少有一般小说中常见的那种对话式描述,而貌似平铺直叙的文字,却将一幅幅活脱脱的生动画面,徐徐展开在读者面前。
“蒋丽莉为程先生,已不知哭过了多少回了。程先生对她在意一点和忽略一点,都是回到房里流泪的理由。那房间重新收拾过了,书本是清洁整齐棵好的。茶杯天天洗;唱片呢,去旧换新,很罗曼的小夜曲;床头挂了些手绣的香包一皮,是王琦瑶的女工;衣柜里也新添了颜色鲜亮的衣服,是程先生的眼光。”
不仅仅王琦瑶,连故事中那个仿佛为衬托王琦瑶而生的蒋丽莉,王安忆也描写得哀婉动人,至于上海那些典型甚至细小琐碎的生活场景,她都刻画得精准到位,“透出一种如烟的尘世感”,让读者不免感慨万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