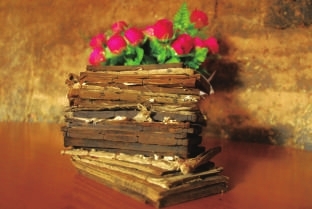通山县黄沙铺镇烽火村峁屏湾,每到农闲时节,村民欢聚一堂,享受一份“听觉”盛宴,听的是故事,听的是乡情,听的是热闹,听的是文化,听的就是说书。
说书,是指用口头讲述历史或传说故事的曲艺形式。这种形式源远流长,宋叫“讲史”,元叫“平话”,现代叫“评书”,江南一带叫“说书”。
在通山,过去盛行说书之风,涌现一大批说书艺人。说书,是通山乡土文化艺术的瑰宝。如今,说书,慢慢淡出山村远离百姓;可是,听书,仍是留存在老辈人心中的最美记忆。穿越时光,走进通山黄沙铺,享受记忆中一道农村文化的盛宴。
说书艺人,
就是村民眼中的“明星”
天冷了,农闲了,黄沙铺镇烽火村峁屏湾村民按耐不住地想听故事了。于是,大家一合计,便又邀请说书艺人到村里说书。常来说书的师傅叫阮绪德、倪世容、石顺龙等人,代表人物是阮绪德,他是阳新县人,由于他是个跛子,人们俗称他“跛脚德”,但并没有取笑的意思。他文化不高,但记性很强,他说书很卖力很生动,情节很吸引人,气氛也很感染人。
乡亲们最爱听的本子有《薛仁贵征东》、《薛丁山征西》、《薛刚反唐》、《罗通扫北》、《杨家将》、《说岳全传》等。在“文革”期间,这些书本都被封死了,说书师傅自然也就不敢说这样的本子,于是《铁道游击队》、《敌后武功队》、《烈火金刚》、《林海雪原》等现代的本子搬上乡村舞台,乡亲们自然也喜闻乐见。
说书师傅到了村庄,男女老少就像碰到了大喜事一样都互相转告,师傅的出现,会给小山村带来一片欢腾,全村上下洋溢着节日般的气氛。他们把说书师傅当着明星,在山上做山活的巴不得太阳早早下山赶回家,有的干脆下午不上山在家睡大觉养精蓄锐,待到晚上听说书,小孩也巴不得早早放学,也想赶热闹,他们对说书的内容似懂非懂,但很喜欢那个场面。淳厚朴实的乡亲们将说书师傅待为上宾,将平时舍不得吃的东西拿出来款待他们,师傅到他家去,别说是吃饭,哪怕是坐一坐全家都很高兴,觉得很有面子。
早早吃过晚饭,人们陆续来到说书的地方,满满一堂屋的乡亲,三五个一伙围着一个火盆。在堂屋里头,摆一张大四方桌,一面牛皮鼓用绳子绑在桌栏上,说书师傅左手拿着鼓板,当地方言叫做“梅花勒”,右手拿着一根拇指大、七八寸长的棍子。桌上还放着醒木、扇子、手帕,还有木剑、木刀、木板斧等,这是师傅的道具。茶壶、茶杯、烟具既是道具也是师傅自用的器具。
往往是堂屋里早已坐满了人,师傅还迟迟未到,这些“发烧友”一个个翘首以盼,就像现在的文艺晚会那样等着明星上台。村民耐心地等待着,等待着 “好戏”的上台……
卖力演说,
大冬天 “说”得大汗淋漓
阮绪德不是不遵守时间,而是故意要人们恭敬地催几次,他才慢悠悠地出来,以示自己的尊贵。一上台,他慢条斯理地敲着鼓,过了碗把茶的工夫,鼓点声逐渐急了起来,这叫“拢场鼓”,意思是催那还没到场的听书人。到了这个时候,观众既紧张又兴奋,他们知道说书就要开始了,那嘈杂声慢慢消失了,小孩也不蹦来蹦去了。可这时,师傅的鼓点又慢了下来,还闭着眼神,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。突然,鼓声骤起,只见师傅立马站起,大喊一声,鼓板朝桌上重重一拍,然后抑扬顿挫的念道:“天上星多月不明,地上人多路不平,林中鸟多叫不停,河里鱼多水不清。各位!话说宋朝陈桥兵变后,众将立太祖为君,江山一统,传至太宗,又至真宗,四海升平,万民乐业,真是风调雨顺,君正臣良。我开卷要讲的是《三侠五义》,首先登场的故事是‘设阴谋临产换太子,奋侠义替死救皇娘’啊……”
这时,村民一个个竖起耳朵仔细听着,有的早就知道这些故事,但还是听得津津有味。在表演过程中,师傅的表情和形态随着故事情节而改变,说到两将交战时,师傅一手拿剑一手挥斧,自己跟自己打了起来,劈劈啪啪的响个不停,他觉得木剑和木斧相击的声音不动听,便在堂屋的角落拿来真斧头和柴刀互相撞击着,撞得声音聒耳、火星闪烁,吓得三岁小孩大哭起来。由于师傅太卖力太投入,就是隆冬季节,也累得大汗淋漓,甚至将棉袄脱掉,只穿一件贴肉褂,衣服还真的湿透了,有的观众戏谑地说,你有狠就将贴肉褂也脱了,师傅说,脱就脱,那些英雄死都不怕,我还怕脱衣吗?说着真的脱了下来。只见他又是一阵厮杀,累得他气喘吁吁、汗珠直流。师傅有声有色,生旦净末丑的声音他也学得十分像,哭起来是泪如雨下,鼻涕掉下来一尺多长,笑起来又满面春风,学马、牛、羊、猪、狗等的声音也是学得惟妙惟肖。由于他是跛子,表演厮杀的姿态格外惹人笑。在那不准说“旧书”的年月里,他就说新书,说得最好的算是《烈火金刚》,说得最精彩的是谢飞骑自行车进城买药与鬼子周旋的那段。
一场酣畅淋漓的表演,让听书者也完全沉浸于说书人的故事中,与主人翁或喜或悲,或笑或哭,或轻歌曼舞,或金戈铁马,或春花秋月,或刀山火海,出神入画地挥洒着人生性情,淋漓尽致地享受着说书艺术……
乐享听书,
村民们共“听”精神食粮
台上,说书人或是清说善讲,坐地传情;或是声情并茂,神色逼真。台下,听书者人头攒动,高潮时喝彩声不断,精彩时掌声持久不停。其实,对说书和听书来说,这不仅是一段欢乐时光,更是一种潜意识的文化传承。
在通山,过去盛行说书之风,涌现一大批说书艺人。说书的时间一般是从晚上八点到深夜两点,到了十点钟,就要休息一刻钟到二十分钟的样子,女主人会为师傅端来一碗糖水蛋,师傅假装连连推托,这不是那种虚伪的表现,而是闹着好玩。师傅端着碗对台下大声喊:洽(吃)——蛋——啦!大家来一起洽(吃)吧。师傅也喜欢卖关子的,说到关键的时候,他就要上厕所,有的人拦他要他将那段说完,他就说,人有三急,屎尿第一,你想我将屎屙在裤裆里呀?他的话总是引人发笑。他的卖关子还表现在当夜要结束的时候,有点像“欲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”的味道,那段扣人心弦的故事讲到节骨眼上,他就戛然而止,任凭人们说好话,他都不肯说了,惹得有的人一夜都睡不着。
师傅说书一般是用方言,但也拗一点普通话和黄陂腔,人们就叫它为“夹屎腔”,意思是半生不熟的。
说书师傅十分辛苦,一夜要说五、六个小时,但报酬很少,在七十年代初,说一夜书是二块钱,没钱就给粮食。到了八十年代一夜书十元钱,九十年代一夜书是二十元钱,到九十年代末期,就很少有人请说书的了,他们的手艺已没了舞台。时光荏苒,时过境迁,徒留那一声声震耳的醒木声空空回荡在山村里,没有了喝彩声,说书也就这样不着痕迹地慢慢消散……
说书,曾是通山农村的一道文化盛宴,给村民带来了丰富的精神食粮,往昔说书时热闹的一幕幕依然萦绕老一辈人的脑海之中,挥之不去。
如今,散打评书、脱口秀等一批新的说书方式,正在以新的内容、新的形式博得更多年轻一代的喜爱。在新媒体的带动下,凋零的说书艺术正在重获新生。相信,那些对说书难以割舍的情思,就如星星之火,终将燎原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