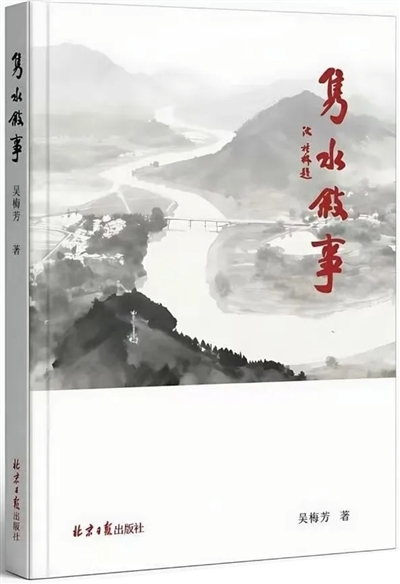读吴梅芳的散文,感觉像在听她拉家常。她用沾满乡土气息的家常话,讲述着一个个关于地域文化、亲情纽带与民间众生的故事,在叙事上褪去了刻意的文学修饰,将“朴实语言”与“真挚情感”深度融合,形成了“以俗写雅、以事抒情、以小见大”的独特风格,如一坛深巷里的陈年腌菜,初看朴素无华,细品却蕴藏着穿透岁月的醇厚滋味。
一、风物与亲情的双重叙事
贾平凹曾在谈及文学创作时指出,一个作家需要有自己的“根据地”,而他的写作深深扎根于故乡商州,其动因源于“一个农民作家苦难生存境遇独有的感同身受”。吴梅芳《隽水叙事》的叙事内容,同样践行了这一理念。其作品始终围绕两大核心——崇阳地域文化与家庭亲情,前者寄寓着对故土文化的敬畏与守护,后者饱含着对亲人的眷恋与感恩,双重真情在朴实的叙事中交织,让散文既有文化厚度,又有情感温度。
在写崇阳提琴戏时,她不仅梳理其从湖南临湘琵琴戏演变而来的历史脉络,记录“杀鸡调”的表演特色,更聚焦于民间戏班的生存状态:白天务农、晚上登台的演员,因戏结缘的戏班情侣,一字不识却能背诵整本剧本的民间师傅。这些细节跳出了单纯的文化介绍,将提琴戏与农民的精神生活绑定——“当他们在炽热的太阳下累得精疲力尽时,扯开嗓子唱一段提琴戏,来一句‘格——格——格’翻高八度的鸡鸣音,惹人发出一阵开怀大笑,全身关节的困乏便一扫而尽了”,让读者看到提琴戏不仅是艺术形式,更是底层民众的精神慰藉。吴梅芳更将提琴戏视作崇阳人的精神图腾,完成了地域文化的精神赋能。
写千年石枧堰,她先以细腻笔触描摹堰坝瀑布“如亿万条春蚕同时吐丝般,将一匹巨大的白练整齐地抛落堰下”的实景,再援引《崇阳县志》还原其千年修建史,重点刻画清康熙年间饶太婆捐银修堰的故事。当她写到“饶太婆为头修堰之前,古堰已被洪水冲坏37年无人维修”,又写饶太婆“捐银百两,令次子王淙为陂正,聚集工匠,费资一千余两,费工五万余个”,将工程智慧与先辈的担当精神融合,让石枧堰不仅是水利遗产,更是崇阳人精神品格的见证。这种“风物即人格”的书写逻辑,是将地域风物转化为乡土精神的载体。
《怀念父亲》中,她写父亲的温和与坚韧:身为大队会计却“没为家里谋过一分利”,农忙时“不见太阳就出工,月亮升天还未归”,晚年耳聋后靠读书看报慰藉心灵。当她写到父亲“担着满满一担农产品和猪肉到城里分给我们兄弟姐妹,两只沉重的箩筐压弯了他的腰,也压痛了我们的心”,平凡的场景里藏着父亲对子女深沉的牵挂。这种亲情书写,印证了谢有顺的观点:“故乡往往会成为写作中的精神维系点”,而“最好的写作,往往都是对童年记忆的一种追念,一种呈现”。吴梅芳正是通过对家庭往事的追念与呈现,让亲情的底色在朴实叙事中愈发温暖厚重。
二、平民视角下的文化传承
谢有顺在散文批评中强调,当代散文应该“更加接近生活”,要“回到事物本身”,以“没有偏见的叙述”关注现实与民间。吴梅芳的散文始终站在平民视角,以亲历者和见证者的身份,书写崇阳大地上的普通民众,尤其聚焦于坚守地域文化的民间匠人,在他们的平凡人生里挖掘不凡的精神光芒。
吴梅芳在“民间文化人”辑中,以平视的目光打量崇阳的文化传承者。写提琴戏国家级传承人甘伯炼,她不刻意拔高其“非遗传承人”的身份,而是还原他90岁高龄仍奔走于乡村剧团、自掏腰包资助戏班的坚守;写他年轻时“每晚都是躲着溜出去,追着蒋春保的戏班,乐此不疲”的戏迷经历,写他文革时期“偷偷藏起剧团服装,坚信提琴戏会有春天”的执着,让读者看到的不是一个“文化名人”,而是一个为热爱奉献一生的普通老人。
写乡村琴痴任子文,她记录其农民身份与制琴爱好的矛盾:白天耕田种地养家糊口,晚上在简陋工作室里刨、抠、锉,制作崇阳提琴与西洋小提琴,甚至发明曲杆二胡获得国家专利。当她写到任子文“收入微薄,一把崇阳提琴只卖得一千多元”,却仍“把一生的心血都融进了琴中”,平民视角下的匠人精神更显动人。还有腿脚残疾却走遍崇阳山水的“摄痴”霍世祥,一辈子搜集民间谜语的“和秀才”王和平,吴梅芳没有用仰视的姿态书写他们,而是以平等的共情,捕捉他们的艰辛与坚守。这种书写,恰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水手、碾坊姑娘,在平凡个体身上提炼着乡土社会最珍贵的精神品质。
三、质朴口语里的烟火真情
蒙田在《随笔集》中曾直言,自己“喜欢质朴自然的言语,饱满有力,简短精练,既不精雕细琢,也不激烈生硬”,甚至主张可以方言土语为文,其核心是拒绝辞藻的矫饰,推崇语言服务于内容本身。这种对质朴语言的推崇,在吴梅芳的散文中得到了充分印证。她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堆砌,没有晦涩的修辞炫技,而是以地道的民间口语和生活化表达,构建起充满烟火气的叙事语境。
在书写崇阳提琴戏时,她用“白天还在割谷呢,晚上一打扮,戏服一穿,往台上一站,小碎步走一圈,水袖一甩,便像仙女了”这样直白的句子,勾勒出民间演员的鲜活形象,没有专业的戏曲术语,却精准捕捉到演员从农妇到“仙女”的身份转变;描写村民看戏的热闹场景时,“好不容易开演了,后边的喊前边的坐下,前边的说最前边的立着我怎么看得见。于是,最后边的就只好站在板凳上了”,完全是乡村生活里的原生态对话,将人群的拥挤与急切的观戏心情刻画得入木三分。这与孙犁散文“淡语皆有味,浅语皆有致”的语言追求不谋而合。
在亲情书写中,这种质朴语言更显温情。《母亲的梦》里写母亲为给父亲治病砍毛棍,“双手被毛叶划得伤痕累累,后来就用破布缝两个袋子‘穿’到手上”,一个“穿”字,将母亲的艰辛与坚韧具象化;《母亲的腌菜》中描述腌菜的制作过程,“除掉根部老叶,洗净,晾干,切碎,晒个大半干,再放进大坛里,一层一层摁紧,洒点盐,直到把坛装满,再用薄膜封口,用麻绳缠了一圈又一圈,防止空气进去”,一连串生活化动词,既展现了母亲的勤劳,又暗藏着童年记忆里的味觉乡愁。
常言道,平平淡淡才是真。吴梅芳以朴实为笔,以真情为墨,在崇阳的土地上写下了地域文化的传承、亲情的羁绊与民间众生的坚守。她的叙事没有时髦炫技的章法,却在“朴实的话”里藏着“最真的情”;没有宏大的叙事,却在“小场景”里见“大格局”。这种创作风格,不仅让《隽水叙事》成为崇阳地域文化的“活档案”,更以动人的文字,抒写了自己对土地与人民的深情凝望。